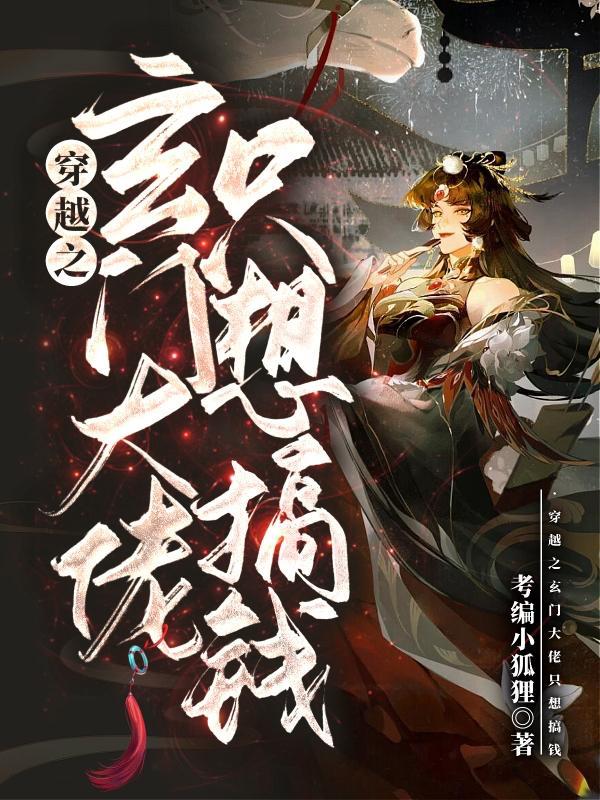592小說網>黃金萬兩【CP完結】 > 第77頁(第1頁)
第77頁(第1頁)
兩日後,明鑒使蘇辭入宮觐見。連一身風塵都沒有洗去,便入暖殿呈報。蕭尚醴面上一絲表情也不見,才登上大位的新帝今日一身常服,國君常服為黑袍,越發襯出手指與面龐的潔白。那柄折扇被盛在金盤裡呈上,這扇曾卡在明鑒司副使咽喉之中,由蘇辭狠心拔出,扇上血迹斑斑,血痕深淺不一。蕭尚醴五指微顫,卻是憤怒已極,強壓下來,閉目令宮人将托盤放下,平心靜氣道:“明鑒司,就被他一人脅迫,整整三日,在嘉陵江頭,不敢進,不敢退,直至他手下開恩,你們才敢回來……”他胸中氣悶,已經逼得肺腑發痛,深息一口氣,走到蘇辭身邊,輕聲道:“你就隻怕他,不怕寡人,殺你們嗎?”他容顔極美,蘇辭這麼一個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人,額上卻有些微汗珠滲出。她腰間挂着明鑒司令牌,差事尚未交差,就如同行伍中人甲胄未解,面見國君隻需行軍禮。單膝點地,低下頭去,道:“陛下容禀:陛下要我死,我自當領死。然而明鑒司辦事不利,陛下問罪,至多斬我及副使孫椎;觸怒蓬萊島主,他殺心一起,劍下不留活口,恐怕明鑒司全軍覆沒,傷的是陛下的耳目。我一人死活是小,隻求保全陛下的明鑒司。”這席話入情入理,蕭尚醴轉過頭去,一步步再走上禦階,袍服下擺無聲掃過光可鑒人的階面,隻道:“遇上了他,算你功過相抵,退下。”蘇辭這才松一口氣,連日趕路,水米未進,起身時險些眼前暈眩,卻還是循禮退出殿外。蕭尚醴背對殿門道:“退下!”殿内服侍的宮人紛紛跪下行禮退出,空蕩暖殿内僅餘國君一人。兩側長龍伏地般的青銅矮爐内燃着銀霜炭,卻靜得連畢剝作響聲音都不能聽聞。他過了許久才轉過眼來看桌案上托盤中的折扇,卻是迫切地展開折扇,沿那被血化開的筆迹逐字撫摸,好僻誰相似,從狂我自知,還未摸到最後一個字,卻将那折扇摔在地上,一袖揮開桌案上茶盞香爐,筆墨典籍,含恨閉上眼,面龐氣得發白。他如對那折扇,有如對自己,對樂逾,既氣又恨,念念不忘地說:“你竟然敢如此對我……你竟然敢如此對我!”說到最後,竟雙手推着桌案,把那桌案推倒。杯盞碎片倒了滿地,桌案轟然倒下,殿外都聽聞響聲,卻無一人敢出聲探問。一盞茶工夫後,才有宮人通傳:“陛下……皇後請見。”皇後請見本來無須通傳,實在是因為蕭尚醴自還是太子之時起,從監國到如今繼位,從未有過這般勃然大怒。宮人都看出這位陛下喜怒不形于顔色,心思之冷漠深沉不下于先帝。皇後初來,還不敢請她入殿,直至田彌彌開口道:“盡管通傳。”宮人才來禀報,暗道皇後果然是國母,與陛下少年夫妻,得陛下信重,絕不是其他嫔妃可比。田彌彌笑吟吟入内,隻見玉階上桌案推倒,滿地金殘玉碎。見到那柄被撕裂的折扇,才遲疑了,思及樂逾,顯出幾分隐隐的憂慮。又笑道:“陛下早有預料,又何必動怒傷身。”她的侍女對蕭尚醴行禮,都挽起衣袖收拾殘局。蕭尚醴一番動怒,背對她輕輕喘息,待轉過面來,兩頰帶些薄紅。他預料到此事樂逾勢必會插一腳,卻料不到……他竟做得如此過分,手起劍落連下殺手重創明鑒司。明知道已經恩斷義絕,往後隻會更無情,卻還要那人如情深意濃時一般,把自己捧在掌上。可他明明已經有了部署要将那個人擒下,遲早有一天,要被他所恨。蕭尚醴美目之中露出掙紮之痛,到頭來冷下心腸,居高臨下望向田彌彌,道:“蓬萊島主庇護弑君的刺客,皇後都看在眼裡。寡人願皇後好自為之,不要像上一回,一心相助異姓兄長。”田彌彌微微一歎,恭敬地伏身行了一禮,道:“臣妾謹記。”蕭尚醴在她頭頂看着,目光一沉,又道:“來人!傳寡人旨意,垂拱令顧伐柯既然不能為君分憂,追剿欽犯不力,即日起褫奪職位。他有病在身,寡人就讓他來錦京養病,若非寡人谕旨,不許再離京一步。”春雨閣主人擔當非議,投靠楚帝,沒想到一子錯,滿盤皆落索。被楚帝禁足在京城内,就像孤注一擲做一件事,卻在事後被人棄若敝履,處境難堪。蘇辭親傳旨意到梁城,顧三強撐起身,由藤衣攙扶,更衣焚香聆聽口谕。面上的神情始終是淡淡的,接旨後便交出令牌,送走蘇辭這人盡皆知得到陛下眷信的昔日下屬。待到人走之後,他才緩慢轉過身,卻勉強一笑,對藤衣道:“和我一起,辛苦你了。”春雨閣内經一場小雪,最富貴閑雅之地也山水蕭索,紅裙侍女都為傳旨退下,更顯得清寂。春雨閣主人被傳入京,不久就要打點行裝上路,藤衣一雙眼睛望着他,握住他的手,貼上面頰,低聲道:“有你在,我不辛苦。”春雨閣之前已放出消息,“惜雨刀”顧夫人早在數年前就登上小宗師境界。得知顧三公子被楚帝處置,已奪去垂拱司大權,“紫金刀”王澄是南楚江湖中用刀的大家,年雖才三十,卻已經十年不再輕易約戰其他刀客。得知“惜雨刀”早已有小宗師修為,卻幾年來留在春雨閣主人身側寸步不離,也不求揚名江湖,便親自下帖約戰顧夫人。一連五帖,言辭懇切,卻被她所拒,顧夫人隻叫人傳口訊。口訊僅一句話,不足二十字,說“外子體弱,樹敵衆多,我若負傷,無人能護他周全”。王澄聽罷撫刀,一聲長歎,道:“‘惜雨刀’是癡情之人。”從此再不提約戰。蓬萊島上,辜薪池掩信深思,林宣輕聲道:“聞說顧夫人素來不放心思在人情世故上,可‘外子體弱,樹敵衆多’,僅八個字便将内憂外患闡明,不卑不亢,還讓’紫金刀’難以糾纏下去。這樣的遣詞造句,多半是出自顧三公子。”辜薪池贊同地點頭,林宣又道:“先生以為?”這一問卻是問,先生以為顧三公子到了怎樣的境地了?許多人都得知他失寵于楚帝,但是他畢竟是春雨閣主人,辜薪池雖不曾與他相見,卻在春雨閣密錄與《蓬萊月聞》中與他有過幾度來往,知道顧伐柯并非等閑之輩,難以想象他會因此就一蹶不振,從此再沒有作為。辜薪池微微搖頭道:“靜觀其變。南楚要對西越用兵,不定……楚帝有什麼密令給他。”說到這裡自己都覺得異想天開,果然聽見林宣忍住的笑聲。林宣道:“是,我會留意春雨閣動向。”十二月二十四日,蘇辭回京面見蕭尚醴。顧三公子戴罪之身,不經國君傳召,自然不能面見。蕭尚醴起身外行,無暇與她細說,隻邊走邊問道:“他還有話要說?”蘇辭想到當時,春雨閣内有人勸顧三公子,上書向楚帝請罪求情。但她明知顧三公子人既聰慧,心氣難免高傲,所謂君既無心我便休,無論楚帝出于什麼原因将他禁足,他都是不會上書求情的。交還令牌時他隻說了一句話,蘇辭俯首對蕭尚醴奏道:“他隻說,‘雷霆雨露,皆是君恩’。”蕭尚醴看也不看她一眼,道:“好一個‘雷霆雨露皆是君恩’。”便向佛殿走去。他曾說過如若為帝便定佛教為國教,以此得到金林禅寺一脈,宗師首徒善忍俯首聽命。繼位之初,就在宮廷中設佛殿,常召善忍至此為他講經,倒是真有意使天下佛門香火恢複周朝時的興盛。他身後随侍一衆宮人,到佛殿外,宮人為他解下鬥篷,他邁步入内。殿外暖陽耀眼,殿内也燃長明燈,佛像寶相端莊。殿内僧侶見他來紛紛跪拜,原本的誦經一時間全停下。僧侶本來隻禮佛不拜君父,金林禅寺尤其如此。蕭尚醴卻對善忍提出一件事,他準僧侶在楚境之内弘揚佛法,興建廟宇,日後更會親自信奉佛法,冊善忍為國師,使金林禅寺成為天下第一大寺,但此後佛門上下僧侶,都要跪拜君主。思憾大師尚未出關,與大師同輩的三位高僧也早不理世事,或雲遊不知所蹤。善忍傳旨回寺,引發一些争辯,還是說動一幹師弟,若楚帝準他們弘揚佛法,就等同于楚帝使世人信佛,有大功德,拜楚帝就如拜人間的如來,也是禮佛的一種。此事因此成為定局。蕭尚醴準善忍在宮内不着禦賜袈裟,那年輕僧人仍然一身白衣,潔淨端正,也躬身拜見,蕭尚醴卻一時不動,他從不在佛前下跪,隻站在佛像前不言不語,眉心微壓。善忍道:“小僧敢問陛下,在憂心什麼?”蕭尚醴道:“寡人在求佛。”他一身常服,曆代楚帝裡唯有他需要以額帶遮掩傷痕,時值冬日,那額帶材質也越發織法密實,竟在絹緞上以絲線點綴精細寶石,織造鑲嵌成金底寶相花紋,被佛前燭火映照,一時繁麗無比。說完這句,便自僧侶手中接過香來奉上,閉上雙眼。這一日照例是與皇後一同用膳,香燃到一半,殿外通報皇後到,田彌彌也走進佛殿,蕭尚醴道:“皇後免禮。”又問道:“阿嫂……如何了?”蕭尚醴的嫂子不少,但能得大楚天子至今還稱一句“阿嫂”的唯有昭懷太子妃。今日蕭尚醴該到皇後宮中用膳,命婦都入宮觐見皇後。昭懷太子妃抱病許久,田彌彌早已免去她每月入宮請安,卻仍然時時過問她的身體。田彌彌道:“還是如舊時,在春芳苑悉心調養着,想來沒那麼快見好。”蕭尚醴知道辜浣病情平穩,一日比一日緩緩差下去罷了,再難有起色,想起以往種種共渡的風雨,不由得在佛前又是一陣沉默。
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,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。
相鄰推薦:緝兇西北荒 愛意收集系統 蝕骨之愛 等一隻鴿子 控制 誰動了我的聽診器 田園醫女:病夫寵上天 快穿之我又有了 信了你的邪 都市異能:我的非人女友們! 王妃的各種寵法 回南天+番外 香蜜之星辰渺渺+番外 原體與崩壞 抗戰:反掃蕩後,我帶回個獨立師 修仙不如跳舞 帶着淘寶去古代+番外 為什麼它永無止境 綜武聊天群:我是修仙的啊 體修弱?我靠煉體鎮壓萬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