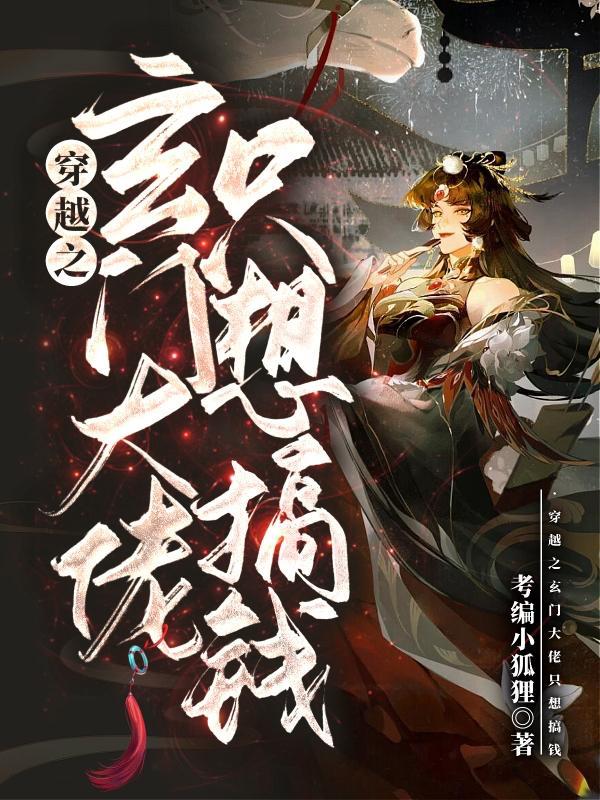592小說網>黃金萬兩【CP完結】 > 第75頁(第1頁)
第75頁(第1頁)
蘇辭目光一沉,秦廣看向蘇辭與孫椎,卻如同駁斥那番基業為重,明哲保身的說詞,道:“舅父說,我江湖人本來重意氣,輕生死,現在江湖要毀,不毀在什麼天子陛下什麼垂拱司手裡,毀在人人珍惜狗屁基業,舍不得身家性命,說什麼留得青山在,誰是青山?你我當柴燒都嫌老。江湖不因幾個名門大派,百年基業而生,隻要有人身上還有血性骨氣,江湖就死不了,畏首畏尾貪生怕死,才是毀了江湖的根基。”梁晚塵再忍不住,一路行來幾度險些喪命都不曾落淚,此時卻掩面而泣,強轉開臉去。秦廣卻對樂逾一拱手,道:“舅父要我代他對前島主賠罪。”雷撼龍從來不信樂羨魚年不滿三十就達到宗師境界,認定她與北漢宗師論武不落下風,必有弄虛作假之處。秦廣道:“舅父說:‘我錯了,大錯特錯!’聽聞島主一人之力敵過水軍,不知大楚水軍為何與蓬萊島過不去,找了《蓬萊月聞》,看不懂,便讓人給他說是什麼意思。他是個粗人,不會說,但心裡就是這麼個意思。他已經把那塊‘南楚第二’的牌匾劈了,說連兒子都比不過,有什麼臉去看不上人家娘?若無此事,已經将牌匾送給島主當柴燒了。”蘇辭靜靜聽着,不為所動也不作怒,聽秦廣道:“舅父說,‘老夫年輕的時候,有人教我唱過一首歌,歌裡的句子我至今記得:少年俠氣,交結五都雄,肝膽洞,毛發聳。立談中,死生同,一諾千金重。’他問島主,島主敢不敢給出一諾,若霹靂堂不在了,蓬萊島是否還會撐起這份江湖意氣?”樂逾道:“隻要我樂氏一脈尚未斷絕。”秦廣道:“好。”竟從腰間解下一把鲨皮鞘的短刀,道:“島主公子的壽宴,霹靂堂不曾到,就以此物贈予小公子。這本是霹靂堂的信物,然而島主既已來了,我便可以回去與霹靂堂共存亡,此物後繼無人,未免可惜。所謂虎父無犬子,便留給小公子賞玩。”他最初來,旁人以為他是擒人;明鑒司來,兩廂對峙,才知他是救人;待到剖白肝膽,短短一席話,他今日來此竟是為将霹靂堂身後事交托。托付完後,大踏步出門,一聲長嘯,竟脫下鹿皮手套,露出一雙如八十老人般蒼老的手,一連扼殺兩人,奪走一匹駿馬,道:“梁姑娘,前路多虎狼,我未能遠送,姑娘保重。”便踏馬揚長而去。兩騎明鑒司之人調轉馬頭要追上,那柄短刀擺在樂逾面前桌上,他一拍桌,桌上粗陶酒杯裂開徑直朝外射去,竟洞穿兩名騎士,血灑雪地,馬蹄疾馳。蘇辭喝道:“不必追!”橫豎此人都是回江北霹靂堂自投羅網送死。江湖相逢就是這樣,遇到一個值得結交的人,有時連一杯酒也沒共同喝過,已經知道意氣相投,可見第一面或許就是最後一面。梁晚塵猶掩着面,秦廣臨别一聲囑咐使她熱淚長流。侯庸看着她,對她如對天人,不敢擁住她安慰,隻伸出手虛虛搭她肩,又匆匆放下手。蘇辭攜部下低語,明知瞞不過樂逾耳力,隻求盡量簡短。樂逾卻對梁晚塵道:“梁姑娘可要我救你?”侯庸驚怒道:“樂島主什麼意思,你說一飯之恩,莫非你不是來救我們的?”樂逾卻一坐,道:“我欠侯兄一飯之恩,卻沒有欠梁姑娘什麼。莫非梁姑娘是侯兄什麼人?”侯庸急忙道:“她是我……”卻仿似啞住,說不下去了。他昔日以為“江晚塵”是個風塵女子,為她建出塵軒,雖不是入幕之賓,但身份也不過是一個恩客。他雖散盡家财相救,但那家财是他繼承來的,不是他胼手砥足掙來的,他對她僅有一腔愛意,自覺配不上她。嗫喏起來,卻沒看見梁晚塵眼中的失望。樂逾道:“既然梁姑娘不是侯兄什麼人,要我救梁姑娘,可以,隻要姑娘答應嫁我為妾。”侯庸怒道:“我以為你是正人君子,卻不料如此趁人之危!”蘇辭卻眉頭一皺,樂逾竟在這要分勝負生死的緊要關頭談納妾之事。樂逾道:“做妾是委屈姑娘。我想讓一個人做我的妻室,但他無論如何不會嫁我。既然如此,若姑娘願下嫁樂某,我便娶姑娘為妻。”侯庸心思大亂,隻道蓬萊島主也對晚塵動心了。他當她如天人一般,也不覺樂逾對她動心有哪裡古怪。隻把蓬萊島主與自身比較,道是别人儀表堂堂,武藝高強,遠在海外又富可敵國,處處慚愧不及。梁晚塵卻想:這蓬萊島主不過如此,無非是要為一段舊年恩怨為難我。她先祖第一任梁侯是周始皇帝的丞相,與樂家先祖有仇。梁晚塵隻當樂逾一心為難她,要報複梁室,也不懼怕,隻道:“島主另有想娶的人,妾身也另有想嫁的人。即使去死,也不會嫁給島主。”她微微一笑,忽然十分溫柔地看侯庸,道一聲:“好不好呀?”她已經握住侯庸的手,侯庸卻連頭也擡不起來,聽她說“即使去死”,全身一顫,隻覺她絕不能死,哪怕是自己去死,也不能讓她死,竟緩緩扯開她的手,忍痛勸道:“樂島主也算你的良配,你……嫁給他,好不好?”她面色驟然慘白,還是笑道:“大抵是我聽錯了,你再說一遍。”侯庸心如刀絞,閉起眼,咬牙道:“你嫁給樂島主,好不好?樂島主,你一定要好好待她!否則……否則我就是死也要拖着你一起死!”這場景極為可笑,樂逾已經仰頭笑了出來,梁晚塵卻笑不出來,她仍道:“你知道我想嫁的是誰,難道,你心裡并沒有我?”侯庸怔怔看她,這話他以往聽到必然狂喜,可為何偏是這時候。梁晚塵道:“為什麼?”他澀然道:“我……配你不起。我配不上你,樂島主這樣的人才配得上你。”梁晚塵猛地擡頭看他,猶如第一次知道他如此怯懦,口中道:“罷了,罷了。”仿佛想打他一巴掌,卻又覺得打也沒意思了,那雙眼極亮,侯庸不敢直視,聽她自嘲道:“我以為你與旁的男人不一樣,到頭來你與旁人沒什麼不同,你能為我死,卻還是以為我是一件玩意,要待價而沽,要旁人判斷我價值幾何,配還是不配!”侯庸一愣,樂逾這時卻已是不笑了,隻見侯庸忽地擡手,自己扇了一巴掌,又是一巴掌。聲響清脆,臉立時腫高。她卻不再看他,對樂逾施一禮道:“請樂島主速速帶他走。”侯庸情急道:“晚塵——”樂逾戲道:“久聞姑娘舞技不下于飛鸾,若姑娘在此為我一舞,使我滿意,即使不做我妻妾,我也願出手相助你二人。否則我隻救一個,真讓姑娘死了,侯兄一頭撞死又怎麼辦?”梁晚塵平靜道:“島主此話當真?”樂逾道:“當真。”侯庸已叫道:“晚塵,你傷勢未愈……”她傷在膝腿,這一生怕是再難以起舞,此時卻決意勉力為之。客棧内不能作舞,她扶牆走出,明鑒司武士與網羅的江湖人士意欲偷襲,卻隻見樂逾衣袖一翻,便倒下四、五個人。衆人頓時滅了這念頭。客棧外風雪交加,卻不聞人聲,隻聽樹上雪落簌簌,她在雪地上試了試。卻見樂逾随後踱出,身量極高,走入風雪之中,更顯喜怒無常,隻道:“飛鸾可在鏡上起舞。”這一句算得逼迫,她膝傷未愈,起舞必定姿态難看。她以舞聞名,迫使她帶傷起舞已是羞辱。冰天雪地尚嫌不足,她舉目四望,隻見一個結了冰的池塘,便道:“那麼妾身唯有在冰面起舞了。”她解下鬥篷,踮腳踩上冰面,錦履底上打滑,如是一想,又彎腰下去,脫了一雙錦履下來,嬌小玉足上隻留一雙雪白羅襪。她臉上傷痕赫然在目,卸下一頂鬥篷,又脫了外裳,身軀又瘦又薄,舉手投足間真可見到袖底領外一道覆一道的傷。可縱使蘇辭看來,她舉動也極為漂亮,她與聶飛鸾一般的幼習歌舞,那歌舞之藝已融入她們一舉一動之中。她沉吟半晌,仿佛在沉吟這一支舞該怎樣跳,到頭來隻慢慢在冰上立起身。傷得太重,跳不出幾個花樣。她走上幾步,步态飄忽,那冰面晶瑩閃爍,在她足下如波濤聚散簇着她,又如雲頭翻滾托着她。叫人想起淩波微步,羅襪生塵——有這幾步,就足以已壓倒許多人畢生所見的歌舞了。可她卻蹙起娥眉,與其說她是以歌舞為生的人,不如說她是為歌舞而生的人,一旦要舞,就要舞得盡興。這一場卻不知要如何起舞。日光映照,冰雪乾坤,她的影子迷迷蒙蒙,映在冰面上。她面色恍惚,仿佛已将生死置之度外,心内隻有這一舞。忽然心念一動,對影一笑,竟憑吊着她自己的影子,在冰面上舞了起來。這一舞本該是為樂逾,為侯庸,此時卻隻為她自己。那山陽先生看着看着,面上突地浮起驚愕,唯有他與樂逾知這一舞。昔年有一隻鸾鳥,三年不鳴,三年不飛,有人聽聞鸾鳥見同類才鳴叫,就在它面前懸一面銅鏡,它以為見到另一隻鸾鳥,高鳴呼喚,奮飛沖向鏡中,撞鏡而亡。這是引鸾舞,便是由樂逾許多代前的祖母傳下,世人不知她小字,隻知姓梁,便以梁夫人稱呼,正是初代梁侯的胞妹。樂遊原與梁侯有仇,就是因他棄官棄位遠去,将周始皇帝多年來的各種賞賜原樣封存,分毫不取,如十餘年前來投靠一般,隻帶一身布衣,幾卷書冊不辭而别,唯一與他同去的人,就是梁夫人。
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,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。
相鄰推薦:王妃的各種寵法 快穿之我又有了 回南天+番外 為什麼它永無止境 體修弱?我靠煉體鎮壓萬古 等一隻鴿子 綜武聊天群:我是修仙的啊 蝕骨之愛 信了你的邪 抗戰:反掃蕩後,我帶回個獨立師 都市異能:我的非人女友們! 香蜜之星辰渺渺+番外 原體與崩壞 愛意收集系統 田園醫女:病夫寵上天 帶着淘寶去古代+番外 修仙不如跳舞 控制 緝兇西北荒 誰動了我的聽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