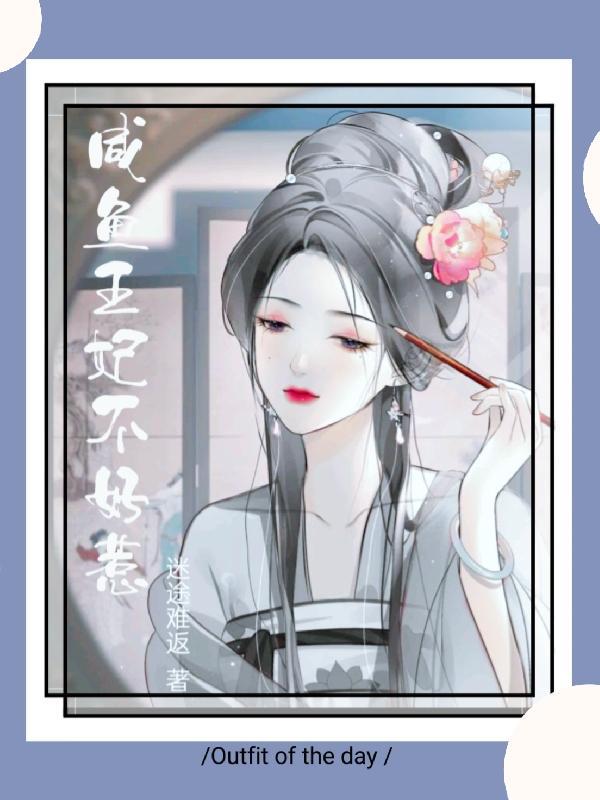592小說網>今年冬天下雪嗎 > 第55頁(第1頁)
第55頁(第1頁)
而與他攀談的一雙男女之中,盛裝打扮過的女人,眼睛就像一刻不眨地粘着他。霜影低眸,瞧瞧身側的桌上有什麼東西,可以打發時間,好等他們聊完。可是,視線又不由自主地,向他投去。
結果,卻是和他閑聊的陌生男人,先發現了她,随後,他跟着轉過頭來,四目相對。
這個瞬間,梁霜影腦袋裡有很多念頭閃過,比如,該不該裝作是一場誤會的掉頭走開。
然而,溫冬逸從褲兜裡拿出手,朝她招了招,再将走過來的小姑娘肩頭攬住,神情語态皆是自然地介紹起來。
這般挨着他有一種微妙的安全感,原先緊盯溫冬逸的女人,眼下正在從頭到腳地打量她,嘴角輕輕下沉,不複剛才的嬌媚。
當身邊醇厚悅耳的男聲,将她介紹成了舞蹈演員時,梁霜影心裡一陣茫然,她不知道面前的男人主業是某企業家之子,副業從事舞台劇的導演,活躍在西方主流歌劇院。而溫冬逸深知,他們玩得隻是一時興起,往好聽了說是陶冶情操,講白了就是閑得慌,哪怕整台劇演得不知所雲,都不缺人誇。
于是,溫冬逸舉着酒杯的手,指了指那個男人,對她說,“他在國外搞舞台劇,有時間可以去試試。”
至始至終,無論是這個說話很浮誇的男人,還是那個撇開頭飲酒的女人,都沒有要追問溫冬逸與她是何種關系的意思。這等心照不宣,仿佛是他身邊一個鐵打的「崗位」,她是流水之中的一瓢。
婚禮儀式在透明的玻璃水台上進行,家屬分兩邊就坐,椅背紗迎着微風飄蕩。
霜影跟着他坐在了正數第二排,斜前方坐的是汪磊雙親,适才他們與溫冬逸打招呼時,還是一派笑意,轉過去面對儀式台,卻擺着一副出席喪禮的臉。
後來,她才知曉,汪磊看着吊兒郎當,沒什麼派頭可言,也是個家底頗豐的富人子弟,而新娘的家世普通,這算嫁入豪門,他的父母自然是不甚滿意,就連上台緻詞,都顯着敷衍了事的态度。
台上女方雙親怆然涕下的講話,台下溫冬逸閑散的坐着,也漫不經心地看着那張漂亮的臉蛋,憂郁隻是眼睛的輪廓,她專注地眺望着别人的幸福。
初見,溫冬逸認為,她美得是仿佛骨子裡有一片豐沛的冰河,你逗弄一下,冰上裂出了花,底下的河水依舊不會有波瀾。然而,那個隆冬的清晨,她站在那兒買早餐,就像淡暖的日光,冷的隻是天氣,他恍然醒悟,沒有哪個大活人,身上淌得血不是熱乎的,所以她會哭,會心碎,眼淚都是滾燙的。
視線落到她素白的手背上,那裡結着一小塊暗紅的疤,溫冬逸微微皺眉,“手怎麼了?”
聞言,梁霜影下意識地擡手瞧了眼,沒甚所謂的說,“燙的。”她對廚藝一竅不通,前兩日在家不死心又嘗試了一次,結果被油花濺到,起了個泡。
他沒再說話。
香槟一開,花瓣一噴,在掌聲之中,白天的儀式算告一段落。大部分的賓客準備回酒店休息,晚上六點還有一場婚宴。
霜影是搭乘度假區遊覽車來的,這會兒跟溫冬逸坐私家車回去,由于司機李鶴軒還在跟新人合影的地方,被人纏住脫不開身,所以後座的他們,沉默以對。
他們之間的關系,不算亂得無法整理,但計較起來又是針尖麥芒,體諒她不想用以卵擊石形容。而她要的是「一時」,因此,不如不提。
坐得近,梁霜影輕輕擺動膝蓋,撞了下他的腿。
溫冬逸轉過頭來,俊美的眼眉捎帶疑惑,“嗯?”
她将一手撐于座墊,直着腰傾向他,似觸碰的親吻,她想撤回原位,卻分開到能聞見對方呼吸的距離,停頓下來。
溫冬逸與她對視的眼眸漸深,似有複雜的心緒流動,她頓覺無望,要偃旗息鼓地退後時,後腦勺有股力量覆來,指引她吻上他,腰後橫過的手臂,又将自己往他的身軀上緊靠。
兩手環過他的頸項,吻到偏頭換了個方向,氣息穩而急,大手滑到她的臀上,讓她抵直了一邊膝蓋,将要坐到他腿上的時候,被突然鑽進駕駛座的人打斷。
撞見這場面,李鶴軒的反應不大,隻為自己的唐突說了句,“不好意思啊。”梁霜影已經把頭埋進他的肩窩,不想見人了。
-
回到酒店,歸置好行裝,霜影站在大床前,環視四周,房間不算大,全開放的浴室占了一半,可是找了一圈,也沒看見一瓶水。她想起了什麼,便出了房間。
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,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。
相鄰推薦:[穿書]小透明的日子+番外 霍先生的妄想症+番外 古穿今之公子遠道而來 獅醒東方 就當老二怎麼了 退休百年,末世大佬被迫再就業 結婚協議[韓]+番外 男友他美顔盛世+番外 快穿之前任在作死+番外 睡前小甜餅短篇集 他心隻存栀子花 玄幻:召喚之萬古暴君 我有特殊的識人技巧+番外 瘋道自傳 (黑籃同人)[黑籃]皮卡丘,這是禁止再賣萌卡! 我為黑暗,當鎮壓萬界敵 影視世界:從在暴雪時分開始 毛茸茸的他 神醫與大俠 寫文之1/2正經[重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