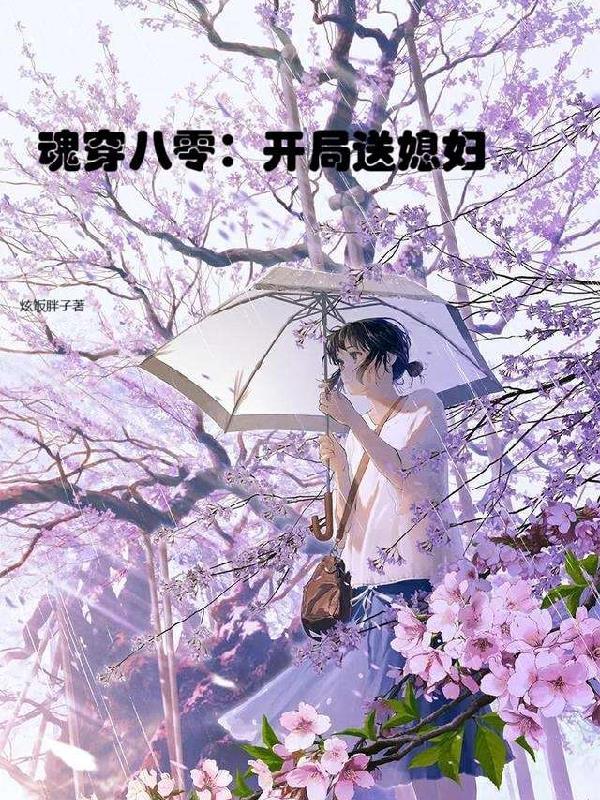592小說網>獨立電影人 > 第49頁(第1頁)
第49頁(第1頁)
他們卷了幾個大包,用自己的床單兜着。謝蘭生背最大的包,小綠也背了一個去。祁勇要拿攝影設備,岑晨要拿錄音設備,飾演“公公”的男演員也會幫忙拎拎袋子,隻有莘野宛如大爺,隻拉他的大拉杆箱。
謝蘭生總覺得莘野這個男人十分神奇。一下了戲,他會立刻穿得宛如電影裡的上流社會,特别拉風,也不管在什麼場合。這不,即使知道等一會兒他們幾個要先坐驢車再坐客車再坐火車,還是穿着深黑的襯衫——左胸有道淺黑的假兜,腰間紮了一條皮帶,跟其他人格格不入。
浩浩蕩蕩地出發了。
…………
盱眙距離北京不遠,第二天,《生根》劇組便住進了北電邊上的招待所。招待所是專利局的,一鋪十元,比較便宜也比較方便。謝蘭生跟前台談好了,從8點到次日8點他們隻用交一天錢。
劇組要先在城區裡拍攝幾場重要的戲,然後再到同學家去完成影片所有内景。
這幾場會在城區裡拍的内容是這樣的:已經有點“不正常”的彩鳳偶然一次進城卻在繁華的大街上見到自己的三女兒了。這裡劇情比較模糊,三女兒在一兩歲時就被丈夫給送走了,按理來說女主彩鳳絕無可能一眼認出來,可傳說中母女連心,她又或許“感覺到了”。總之,她在街上所見到的究竟是否是她女兒,或者不是她女兒,片中沒說,也沒有任何暗示,重要的是彩鳳自己認為是,從而崩潰。
因為那個小女孩兒正倒立着引人關注,面前放着搪瓷缸兒,在乞讨。而搪瓷缸兒的下邊還鋪開着一張白紙,頗幼稚的筆迹寫着:【我的爸爸重病在床……】
半晌,女孩胳膊開始發抖,最後終于堅持不住,一頭栽下來,磕在地上。而當女孩爬起來時,彩鳳看見,她的額頭、臉頰、小臂、手肘,全都是傷,縱橫交錯。她每天就倒立、受傷、再倒立、再受傷,苦海無涯,走不出去。
看到這些她沖過去,被攔住了,她大叫,接着,一個男人走進場地抱起女孩匆匆離開。
彩鳳回到自己家後就一直都瘋瘋癫癫的。
小演員是雜技團的,當初,謝蘭生一說要拍戲就有孩子拼命舉手,毫不費力。而幾個大人,而由攝影師、錄音師等自己人客串了。
這場拍完,衆人全都有些壓抑。
“囡囡,”謝蘭生想轉移話題,“到北京了,在首都了,有沒有啥想看看的?馬上就去梨樹鄉了。”
“唔,”囡囡立即想起來了,道,“想看一看天安門!看一看升國旗!”
“升旗是吧?”謝蘭生是北京土著,他上學時被組織着看過N次升國旗了,對各季節開始升旗的時間還比較熟悉,他算了算,說,“那這樣吧,咱們明天六點左右出發,騎自行車去天安門。沿着西海走,半個小時應該能到,正好趕上升旗儀式。然後咱們随便逛逛,八點來鐘往回騎,跟劇組彙合去梨樹鄉。”
“我……”歐陽囡囡說,“我不會騎自行車啊。”
謝蘭生說:“我馱你去。”
歐陽囡囡終于高興了:“行!”
定了行程,謝蘭生便轉過腦瓜問劇組的其他主創:“莘野,祁勇,岑晨,歐陽囡囡想看升旗,你們去嗎?”小紅小綠也是土著,被一朋友介紹來的,就不用問了,肯定看過。
祁勇岑晨都說不去,時間太早了,隻有一向愛看熊貓的莘影帝很感興趣。莘野比較想坐Taxi,但也不會矯揉造作,謝蘭生說騎自行車那大家就騎自行車,他也會——為出行方便,目前《生根》整個劇組一共有兩輛自行車,是導演謝蘭生回家蹑手蹑腳推出來的,他自己騎着一輛同時用手拖着一輛把車帶回到了劇組,當天晚上打電話時母親直說要打死他。
…………
就這麼着,第二天的早上六點,蘭生莘野歐陽囡囡三個人騎兩輛車子從招待所往天安門走。莘野還是風騷無度,穿着深藍的襯衫,騎在黑色的“二八”上,身高腿長,矜貴又懶散,周圍的人全在看他。
一開始是謝蘭生馱歐陽囡囡,不過上了長安街就換成莘野帶囡囡了。
到天安門時間正好。他們把車鎖在樹上,擠進人群,看升國旗。歐陽囡囡特别激動,眼神發亮,一直說:“謝導,我想演戲,我想出來,我不要再回鄉下了。”她的眼睛閃着神采。
謝蘭生隻拍拍她頭,說:“囡囡,想當演員還是必須要學念書,等過幾天各奔前程也要複習學的東西。《生根》拍完以後,我就不能盯着你了,你要自己督促自己。”
歐陽囡囡用力點頭。
一個鄉下的女孩子一頭撞進另一種生活,她想捉住,雖然很多時候她無能為力,唯有聽天由命。
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,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。
相鄰推薦:人類觀察計劃+番外 讓你兼職賣貨,你全上交國家? 他太A了,我好慌 我是個總裁我莫得感情 超喜歡你 假戲真做後太子翻車啦 男神,滾粗 孤獨的靈魂 今天能不能躲過柯南的麻醉針 我在古代直播,為末世基地賺物資 你饞的是皇位麼 盜墓從兜比開始 别反野了,對面打野都哭了! 反派失憶之後+番外 這個Omega全異能免疫 諸位艱難求生我躺着狂暴刷 侵占 多元時空 太子寵妻有道 奪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