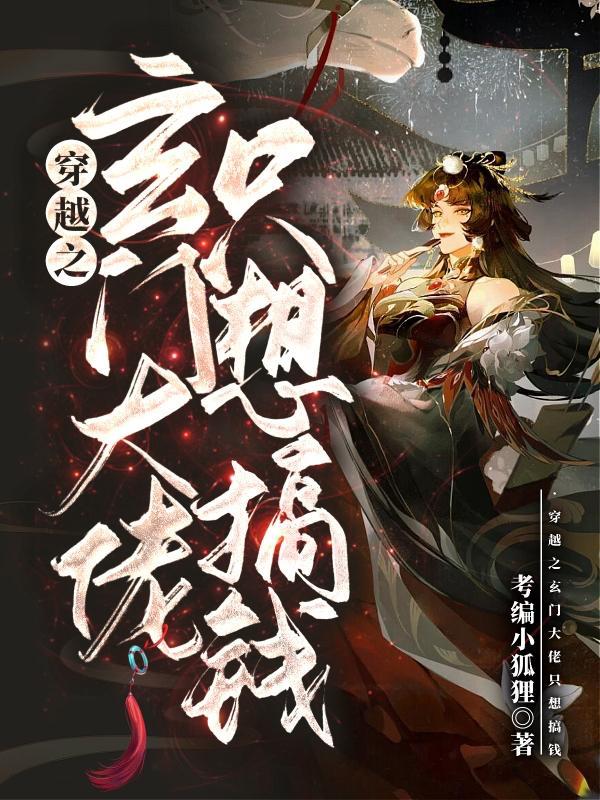592小說網>黃金萬兩【CP完結】 > 第149頁(第1頁)
第149頁(第1頁)
楚帝與皇後一夜長談,次日朝會,立素王蕭醍為太子。令宗伯拟定佳期,為太子加冠、大婚。常人之子弱冠之年而加冠,帝王家之子卻不必非要滿二十。加冠才是成人,成人才能處政,蕭尚醴便是十七歲為太子時行冠禮,之後大婚。大楚威鳳九年二月,太子蕭醍年十六,娶吳王同胞姐、嘉陵郡主田氏為妃。三月,楚帝禅位于太子,其時楚帝年二十七,朝臣驚悚,以陛下春秋鼎盛,因何禅讓為由三奏請,太子更是長跪于殿外,請求天子收回成命。楚帝卻心意已決,稱他“本為諸子”,便是本為尋常皇子,因昭懷太子病逝,齊陽王英川王因争鬥而死,壽山王又造反,這才履位登基。如今天下安定,他年号為“威鳳”,繼位之初,國中有玄鳳現世的祥瑞。但他數月前夢見玄鳳飛去,麒麟獻玺,因此有了感悟,要退位讓賢,從此在太安宮中靜修,除皇後外,其餘人等一概不得打擾。也不顧他這樣退位會留一個怎樣的千古之謎,又會使後人生出何等猜測。這一年三月底,無人知曉,應在太安宮靜修的陛下已不在太安宮内。蕭醍在大興宮中,拒不繼位,群臣對太上皇心懷畏懼,不敢勸太上皇不禅位,也見不到太上皇,隻能一日三奏請求儲君舉行登基大典。蕭醍卻堅持道:“父皇尚在,父皇才是天子,我豈敢穿父皇之衣!”縱使新制了冕服旒冕,他也堅稱天子冕服與十二旒冕都是父皇的,他不能穿戴。離錦京之前,蕭尚醴曾問他:“履位九年,寡人可擔得起嘔心瀝血、殚精竭慮八個字?”蕭醍也是如此跪求,道:“父皇擔得,兒臣知道父皇的勞累,但正因擔得,兒臣才更要請父皇不要抛棄天下萬民。”蕭尚醴心中卻道:我沒有這樣重要。若大楚隻能仰仗一個人才不至于衰落,就不是他想見到的大楚。他平淡道:“我是寡人,并無仁心,你比我有仁,苛政之後,大楚需要一位仁君與民休養生息。”不待蕭醍再語,他又道:“你母後英明剛斷,若為男子,必取吳自立,為一世之雄。今我去後,你需敬而重之,如有政事是她一力主張,痛陳利弊,你要聽從,不可理會女主幹政的物議。”蕭醍無法阻攔,可直到蕭尚醴已到梁城,還接到蕭醍追來的書信,乞求他回心轉意,不再禅讓,回到錦京。蕭醍直至此時才猜出他為何要禅位離宮,含蓄卻懇切地勸告他,以天子之尊下嫁一個男人,雖眼下世人不會知曉,但一百年後,兩百年後,萬一被後人因緣巧合得知其中隐秘,他将聲名盡毀,淪為笑柄。蕭醍追去四張絹帛,卻隻收到一張回覆。那一張絹帛上空無一字,蕭醍慢慢閉目,知道這位父皇心硬如鐵石。被後人所知又如何,他對今人後人将如何看他都不關心,無話要說。大楚威鳳四月七日,太子終于繼位,沿用太上皇年号至次年再建用新年号。四月九日,一艘樓船抵達蓬萊島。時是午後,一個藍色衣衫、容貌秀美的文雅青年前來,笑道:“在下林宣,蕭……”他原想說蕭陛下,但思及這位蕭陛下已抛開帝位,島上諸人也不知他的身份,便改以“先生”相稱,道:“奉命送來納采之禮,也代為問名。”告知他蓬萊島上婚儀早已準備妥當,島主隻待他來。又關切詢問一路船行可好,車馬是否勞頓,道是島主十分挂懷,态度溫柔和悅,不多時便退下。婚有六禮,他的逾郎自不會有疏失,林宣送來納采之禮,禮為雙雁,取雁若伴侶死就不再擇偶,以示忠貞。問名除問名姓外更問生辰,帶回庚帖相合。林宣送回庚帖,略一留意,就見那位蕭陛下的庚帖上寫的名姓是“蕭靜”。此後是納吉、納征、請期,納吉是祭祖占蔔,納征是下聘,請期則是仍令使者告知佳期。這些事原可以不做,樂逾卻知他重禮儀,甯願倉促也要一一做到,應當分為許多日做的事在一個午後完成。餘下的一項就是親迎了。蕭尚醴如在夢中,軒外樂聲傳來,婚禮也作昏禮,應在黃昏時舉行,鼓樂卻可早些興起。蓬萊島上賀者衆多,有作催妝詩的習俗。便是恭賀觀禮的親友盈門,新嫁娘卻閉門不出,借口梳妝,新郎催嫁,就要說成催新婦梳妝。新郎寫詩來催,親友也要一齊幫着寫詩催促,直到被催之人覺得足夠,才開門上車,讓新郎迎走。軒内早已堆滿聘禮,都是奇珍異寶,黃昏将近,侍女點起燈燭,更映得滿室聘禮寶光燦爛。大門緊閉,門外已有湊熱鬧的賓客争誦催妝詩,不是“借問妝成未,東方欲曉霞”,就是“何須面上濃妝畢,留得雙眉待新郎”,不是借問梳妝何時好,你看時辰已晚,東方都要升起曉霞,就是勸新人何苦梳妝呢,留下雙眉,待新郎為你描畫豈不最好,誦的無不是風趣诙諧之句,守門的侍女都不禁笑成一團,卻還是拉下臉不開門。蕭尚醴卻不知為何,明知要下嫁,初時不覺,聽催妝詩卻聽得越來越……羞赧,雙頰發燙,鏡中竟有幾分紅,幸好旁人不能覺察,隻當他還面色淡淡,不過尋常。親迎的時辰還未到,八面風來閣中三四個人在陪島主寫催妝詩。蓬萊島上校書郎雖多,能陪樂逾寫催妝詩的卻不多,林宣下筆不停,寫過一首,請旁的校書帶走,送去軒外由賓客誦讀,含笑道:“再寫下去,島主或許文思泉湧,晚生卻要文思枯竭了。”樂逾已換上婚服,遵周制,戴爵弁冠,纁裳缁袘。爵弁便是他加冠時發冠,如天子諸侯的冕而沒有垂旒,缁是黑,纁是玄中帶黃,便是缁纁二色的深色衣裳。婚服莊重,此時動筆的姿勢卻不甚莊重,林宣好奇去看,就見他寫了一沓,卻都是“再顧連城易,一笑千金買”“隻要君流眄,君傾國自傾”“妝罷含情坐,春風桃李香”之類的句子,後來卻連這樣的句子都寫盡,有些厚顔起來,道是“胸中自有催妝句,紅羅帳裡與細論”,意是催妝詩句我自然是有的,卻不在賓客前誦了,留待紅羅帳裡,夜半無人,耳畔細說。林宣忍笑給辜薪池看,道:“若是親迎的時辰到了,那位還不出門,島主又待如何?”樂逾隻道:幼狸此來不易,承蒙下嫁,他若羞成那樣,我自然不會勉強他,心甘情願等在門外,一笑又問道:“小蛾去見他了?”卻說另一面,大門緊閉,窗中卻忽然打入幾顆東西,打在他背上。侍女驚呼,争向窗外看,蕭尚醴避開擡頭,卻見打到他婚服上的是三粒鮮果,自順滑如水的衣上滾落地面,白的色如凝脂,紅的豔如瑪瑙,竟是紅白兩色櫻桃被當作彈丸。這時節不是櫻桃果熟時,待到櫻桃成熟至少還有一個月。早早催熟的櫻桃十分罕見,卻被一個孩童興沖沖拿來打鳥兒打人——倒是頗有情緻——蕭尚醴轉瞬心裡一跳,猛然想起曾送過濡兒臂弩。他不敢置信地看向窗外,一株花樹上,一個十歲的孩子看不見面孔,爬樹又爬窗,“哎喲”一聲地從窗裡滾進來,蕭尚醴立即扶住他,見樂濡面容有些委屈,莫非受傷了?那清如水的雙眸望向他時,卻憑空來了精神,眼睛一亮,眉開眼笑,搭讪道:“大美人,你要嫁給我父親嗎?”他曾做過中原天子,被這個孩子調戲了,卻生不起氣。那孩子衣上有些泥塵,下擺與小白靴也沾髒了,可容貌在這日暮的室内仍如冰雪美玉一般,熠熠生輝,唇紅齒白,與他相對便如與年幼時的自己照鏡子。那稚嫩柔美的眉眼他決計不可能認錯。卻聽樂濡為難地求道:“大美人……”蕭尚醴低柔道:“怎麼了?”樂濡哭喪着臉道:“我,我偷偷來看你,被你看到了。父親和惠娘一定要罵我。”他靠在蕭尚醴懷裡,像一隻進退兩難的幼貓,五官皺成一團,差一點就要咬起指甲,哪裡認得出眼前這大美人是他見過的楚帝,又哪知這一見多麼艱難。蕭尚醴十分心軟,放緩聲低柔道:“你見了我,逾……你父親一定不罵你,也不讓别人罵你。”那孩童進不得退不得,看看侍女又看看蕭尚醴,仿佛覺得眼前人可靠,撒嬌道:“你真好。父親說,我以後可以叫你義父了。”蕭尚醴輕輕抱住他,心頭激蕩難言,樂濡趴在他懷裡,也覺蕭尚醴是他生平十年,所見第一漂亮的人,又眼熟親切,忍不住低頭嗅一嗅他,身上還有一股香氣。就閉上眼張開雙臂倚靠在蕭尚醴懷中,面頰舒服地在他衣上蹭了蹭。待到侍女歡喜通報:“島主來親迎了!”樂濡慌張道:“義父,我們說好啦!”就趕在父親趕到之前一股煙溜了。蕭尚醴隻覺胸口跳得生疼,想要立即起身,卻動不了。面色暈紅,指尖卻扣在掌心發涼發顫,隻聽着逾郎的聲音。那不疾不徐,低沉舒緩的男聲全是寵溺愛惜,道:“美人一笑值千金,一步自然值萬金。你是‘昭陽第一傾城客’,我為你鋪了一條萬金之路,你可願出門一看?”那門緩緩打開,侍女行出立在兩側,然後才是一個人慢慢走出。正是日暮黃昏,落日金光照在蓬萊島上,蕭尚醴的住處本是羨魚夫人的住處,羨魚夫人去後,樂逾下令閉館不開,卻為蕭尚醴重新開啟,更名為昭陽館。此時自聞琴軒至昭陽館,路途上皆鋪錦繡為毯,以使蕭尚醴衣履不沾塵埃。毯上又切金為薄磚,以萬兩黃金為他鋪路。在這落日時分,錦繡與黃金輝煌燦爛,金光如焰火一般照人。
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,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。
相鄰推薦:控制 回南天+番外 王妃的各種寵法 誰動了我的聽診器 香蜜之星辰渺渺+番外 田園醫女:病夫寵上天 抗戰:反掃蕩後,我帶回個獨立師 綜武聊天群:我是修仙的啊 都市異能:我的非人女友們! 原體與崩壞 蝕骨之愛 帶着淘寶去古代+番外 等一隻鴿子 為什麼它永無止境 修仙不如跳舞 信了你的邪 快穿之我又有了 體修弱?我靠煉體鎮壓萬古 緝兇西北荒 愛意收集系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