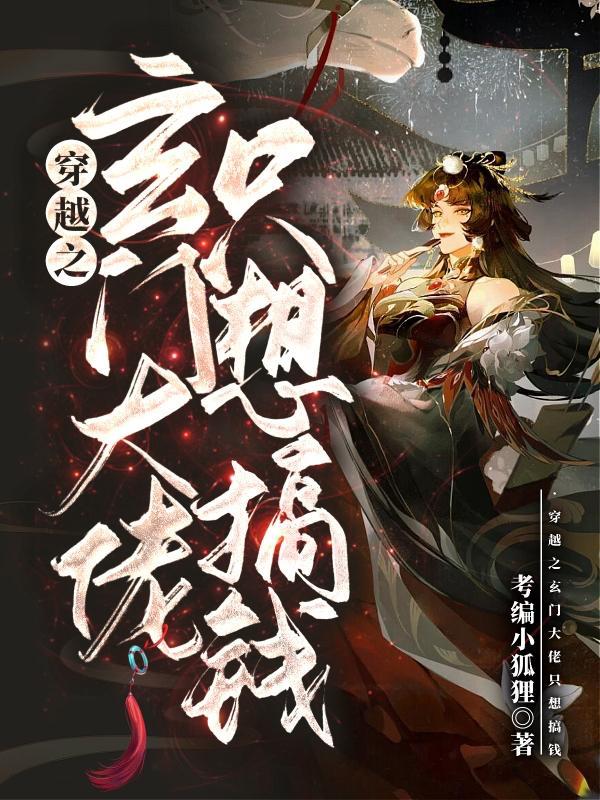592小說網>黃金萬兩【CP完結】 > 第15頁(第1頁)
第15頁(第1頁)
所有對“淩淵”心存疑問的人可不是都要來問他春雨閣了!顧三被打個措手不及,隻得認下這筆倒黴糊塗帳。誰叫這蓬萊島字号最響亮的兩個人有志一同訛上他了!藤衣呈上幾張名帖,冷冷道:“自公子手上新一期《蓬萊月聞》印訖至今,不過半日,已有三份匿名帖來問‘淩淵是誰’,方才又有兩份,連匿名也不要了,直接署了北漢講武堂與東吳萬珍樓的款。公子要如何回複?”顧三怅然地摩挲腰間玉佩,道:“隻有……唉,不必一一報價了,挂出牌去,此一問亦屬萬兩黃金之列。”藤衣遲疑,道:“公子,若是如此,難保江湖中人不揣測你故弄玄虛。”“可我又能如何?”顧三嗟歎:“總不能直言,‘淩淵’即是樂氏島主?樂逾覺得他虧了,我還覺得我虧了呢。不過,”他悠悠含笑,雙眉就化作遠山,“要是能為靜城王争取到蓬萊島這個奧援,我這一番‘萬兩黃金’的造作倒也造作得不虧。”藤衣被他眉眼之間的舒心惬意迷住,不由得睜大眼睛:“那麼公子以為,靜城王殿下能夠赢得蓬萊島主歸附?”顧三溫柔耐心地望着她的雙目,說與她聽:“歸附不一定。靜城王要是夠聰明,自然會摸準樂逾的七寸。更何況他聰不聰明不說,那位太子妃對樂逾所知甚深,必定會為小靜城王出謀劃策以收服蓬萊島為己用。你我且看着,樂逾總以為他能置身事外,可我看來,隻怕從與靜城王傳話交談起,他就已經陷在這裡頭,不脫一層皮無法抽身了。”藤衣安靜聽他的話語,專心緻志,不置一詞,雙目澄澈如一池秋水,兩片精巧的耳垂上各綴一點明珠,閃閃如波光耀眼。顧三心中一動,放開名帖,柔柔握住她的手,她低頭看着,亦沒有掙開。這世上他可以對着直抒胸臆的隻有她一個。顧三心思數轉,倒也沒什麼對樂逾的愧意。此番他要是算不到樂逾,能脫身而去是樂逾的本事;他要是算到了樂逾,使靜城王從此得一強援,那也是樂逾自投塵世的羅網,願打願挨了。人間至繁華富貴處,傍晚時分,萬燈齊亮。仙壽宮樓台欄杆多以漢白玉搭建,如晝燈光将含香殿映得一片通明。侍女張燈以後躬身,一個年約四十的女官看着天色,又有一排侍女捧着禮盒,躬身道:“季女史。陛下駕到,又賞賜許多東西,需存冊入庫。”容妃是周朝遺下的唯一一位帝女,周朝國姓為虞,帝女小字柔姿,封永懿帝姬。傳聞周後夢遇神女引她觀優昙婆羅花兩度盛開凋謝,懷上容妃與她的孿生妹妹德徽帝姬虞貞質。周室以昙花為祥瑞,末年民不聊生,周天子還在搜集天下昙花,終使暴民騷動,攻入行宮,周室血脈一夜間淪喪殆盡,史稱昙花之亂。沖入行宮的亂民見到她,為逃難形容狼狽,那容光卻宛如明月在天,竟都瞠目結舌紛紛退後不敢朝她動一根指頭。她如昙花一般,美到這個境地,已經不能以論容貌,仙姿獨絕,氣韻高雅,一身衣裳如雪中輕煙鋪百花。楚帝年過五十,鬓發斑白,細緻地一把抓住她的手,用掌心暖熱愛妃的指尖,道:“入春多時,手還這樣涼。今年這是怎麼了?”容妃謙恭道:“妾身向來如此。血氣不足,是早有的事了。加上近日又為醴兒的事擔憂。”楚帝愠怒道:“寡人與你的兒子,上天都要庇佑,誰敢讓他有一絲一毫的不好?”他思及已故的太子與靜城王被刺,拍了拍掌中的手,道:“你放心,寡人絕不會讓醴兒出一點意外。”便在這時,太監通報靜城王在殿外候召。楚帝斥道:“還候什麼召,請靜城王進來!”宮人都心驚膽戰,雙膝戰栗。恰好季女史前來,見狀去請靜城王。靜城王入内欲拜,被訓斥過的太監連忙攙扶,還未拜下,楚帝已道:“免了。快來讓你母妃看看。”蕭尚醴唯有止住行禮,上前走到容妃面前。兩人容貌宛如姐弟,她一雙手托起幼子面龐,細細凝視他的臉,良久輕聲道:“下次不可以廢禮數。”蕭尚醴在她膝邊依依跪道:“是。”又仰面望向楚帝,道:“兒臣有一請。”容妃也望了楚帝一眼,歎道:“不要仗着你父親的寵愛,諸多要求。”楚帝開懷笑道:“兒子向父親讨要恩典,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!說吧,寡人的靜城王又想要什麼?”蕭尚醴低頭道:“兒臣想要一位老師。”容妃蹙眉道:“醴兒,你有自己的太傅。”蕭尚醴道:“靜城王太傅代兒臣管理封地,不在京中已久。兒臣覺得自己……學問處事上都有欠缺,想要一位可以随時請教的老師。”容妃仍不松口,道:“諸皇子并非都有太傅,你有靜城王太傅,已經是君父例外的恩寵。如今又要陛下再給你指一位太傅嗎?”蕭尚醴道:“兒臣不敢。”一雙黑漆漆的眸子浮着一些委屈,稍縱即逝,他平靜道:“兒臣想拜一位先生,他是山野之人,并沒有入仕的志向,不需太傅的職銜。隻是,兒臣以為,拜誰為師,需要先得到父親母親的準許才能去做。”“寡人還以為是誰,哪怕是寡人的相國,醴兒想要他做老師,寡人都能立即下令。卻原來是個山野之人!”楚帝笑道:“所謂在野名士,多是沽名釣譽之徒。罷了!既然醴兒喜歡,你想拜誰為師,都由得你了!”蕭尚醴下拜,道:“謝父皇。”心中暗喜:我是一朝國君的愛子,我若願意對誰以禮相待,加之以師長的尊榮,即使是蓬萊島主,也絕不能拒絕。一片樓閣通明的宮殿外,一個皇子衣飾的年輕人在紅廊下待宣。身材颀長,儀容俊雅,兩個内侍伺候在側,正是壽山王蕭尚醇,排行第六,比靜城王年長三歲,才過弱冠,已博得賢王美名。蕭尚醴由内侍引路,本來步履輕快,見壽山王便停住。他與壽山王非同母所出,壽山王是和妃所生,和妃八年前身逝,壽山王因母妃常年無寵,郁郁而終,對享盛寵三十年不衰的容妃多有記恨。他雖未表露在面上,蕭尚醴卻隐約能察知,因此與這六哥素不親善,這時迎面相對,避無可避,才寒暄道:“六王兄怎不入内?”壽山王道:“本王自是不如九弟,還要在此聽宣。九弟、母妃在殿内與父皇一家團圓,這領事内監都不敢通報打擾。”蕭尚醴道:“六哥何必這樣說。”言下之意不以為然,壽山王暗覺不悅,畢竟靜城王母子受寵,便也立即改顔相向,道:“愚兄說笑罷了,父皇與母妃怎不留九弟用膳之後再走?”“免了……”蕭尚醴道:“小弟還有些旁的事。”他方才得到父母應允,一刻都坐不住,還被容妃輕聲責備。壽山王道:“哦?”瞟他一眼,以己度人,腹中盤算道:他怕是也得了南楚将與東吳締結盟約一同攻越的消息——這九弟裝得一副不解世事不理不搶的模樣,現下太子英川王齊陽王都不在了,他也争着冒起頭來。壽山王負手笑笑,叮囑道:“那麼九弟慢走。叫下人仔細伺候打燈,當心路。”這一日壽山王蕭尚醇入宮面君正是為與東吳結盟一事,入夜時分,壽山王甫一回府即刻令人去請壽山王太傅魯行緻。魯行緻聽聞壽山王府下人語聲惶恐,打點精神入書房,果然見一地散落的物件,書案上香爐鎮紙紙筆全數掃落在地,壽山王氣極笑道:“父皇今日居然說,靜城王要再選一位太傅,哪怕要當朝相國做他的靜城王太傅,父皇也即刻為他下旨。——父皇為何不直接将這帝位給了他!還要我們這些兒子搶什麼?”待壽山王散盡了郁氣,半晌,魯太傅開門令跪在外的婢女再奉茶入内,言道:“殿下何必大動肝火。陛下偏心也不是一日二日了。”壽山王自嘲道:“本王的母妃病重沉疴時,父皇在仙壽宮裡,隻因蕭尚醴那小兒夜半驚悸,他一住就是半月,聖駕日日在仙壽宮。關起門來,做一家三口人。”他咬牙切齒道:“從那時起,本王就想知道,同是父皇的兒子,他願做靜城王的慈父,為何對本王母子如此涼薄。”魯行緻欲語,如今當務之急是聯絡東吳,而非自怨自艾。壽山王豎起手示意他不必多言,徑自道:“言盡于此,太傅安心,從今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的隻字片語。本王可背不起一個怨望的罪名。隻是皇天在上,若有一日本王登上帝位,必定要誅殺那亡國的賤人及賤人所出孽種。”次日晨起,綠竹堂醫館仍是門庭冷落,日光穿堂入戶,殷無效靠坐在案邊蒲團上,一徑入神讀醫書,一徑揭開白汽蒸騰的藥壺蓋,随手扔入幾錢稱量好的藥材。如是幾回。近午時,樂逾才仰面從竹床上爬起,攏了攏衣襟,行屍走肉一般拖着腳步走到殷無效對面坐下。殷無效遞給他一碗藥,道:“頭疼吧?叫你不要亂動我的藥酒了,喝了沒好處。你自恃酒量好,趁我睡着把我的藥酒全喝光了。活該你頭疼。”樂逾接過那碗,仰頭一飲而盡,殷無效道:“小心燙!”樂逾扔開那藥碗,道:“你問過我薪池和顧三我更信誰,我可曾對你說過,薪池如茶,顧三似酒?”
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,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。
相鄰推薦:綜武聊天群:我是修仙的啊 帶着淘寶去古代+番外 抗戰:反掃蕩後,我帶回個獨立師 誰動了我的聽診器 控制 信了你的邪 都市異能:我的非人女友們! 快穿之我又有了 回南天+番外 王妃的各種寵法 等一隻鴿子 香蜜之星辰渺渺+番外 田園醫女:病夫寵上天 為什麼它永無止境 蝕骨之愛 緝兇西北荒 體修弱?我靠煉體鎮壓萬古 愛意收集系統 修仙不如跳舞 原體與崩壞